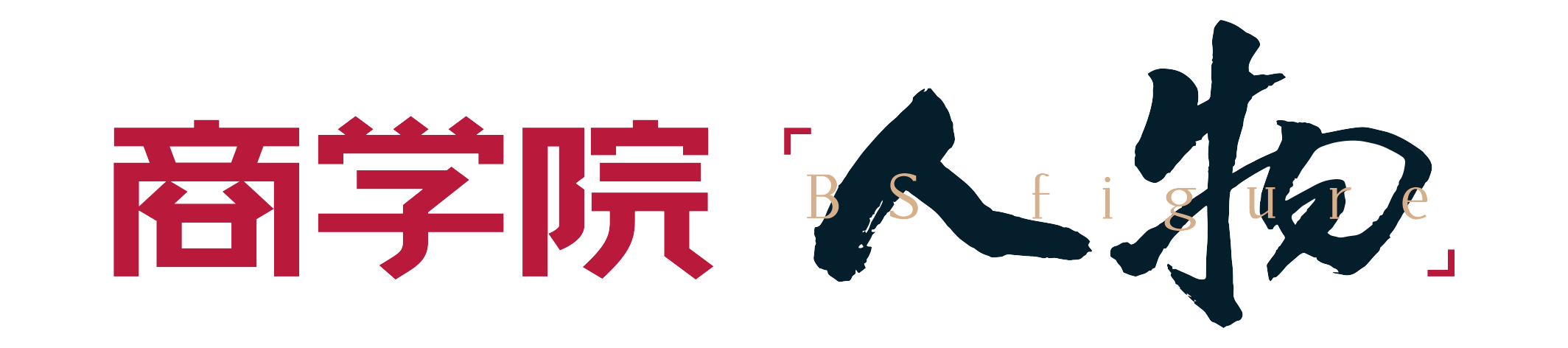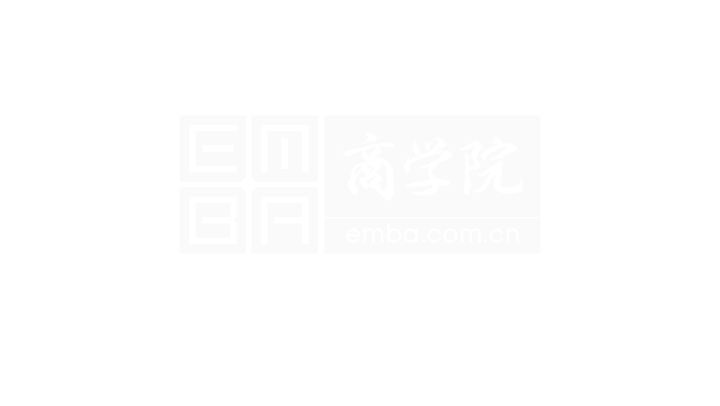北大国发 | 【对话】伍晓鹰 刘国恩:经济增长的千年密码与当前难题

题记:2023年4月19日下午,承泽论坛第12期暨北大博雅讲坛第510期——“探寻长期经济增长的密码 ”暨《世界经济千年史》新书悦读会在北大国发院承泽园举行。本期活动由北大国发院和北大出版社联合举办,也是世界读书日特别活动。本期邀请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增长实验室主任、《世界经济千年史》主译者、日本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原终身教授伍晓鹰带来深度分享,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点评并对话,财联社副总编辑王全宝担任对话环节主持人。本文根据对话环节的内容整理。
本书有何独到之处?
王全宝:请问刘国恩教授,您对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这本书以及伍晓鹰老师的演讲有何点评或补充?
刘国恩:点评不敢当。在过去的研究中,但凡涉及国家经济的长期增长,特别是跨国经济增长的历史主题时,除了在麦迪森的书中寻找可以引用的数据,我几乎别无他选。在课堂上我也曾跟学生们讲过,麦迪森这一部巨著中的统计数据,好比是一架飞机摔碎之后又重新拼起来,拼接之中难免会有不准确甚至是错误之处,但若想了解人类在过去两千年纵向和横向的经济增长足迹,基于我所有限的认知,目前还没有任何一本著作能替代此书。
伍晓鹰老师提到,本书是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用定量的方法来解读人类经济发展史。无论是研究宏观经济增长还是研究经济史,这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从中可以学到麦迪森的分析,其更大的贡献在于为社会提供了一种数据公共产品。对世界经济感兴趣的人可以从书中找到可知可用的数据,在此基础上做出自己的诠释。这也是该著作与其他学术著作的区别所在,把学术研究和公共产品两种功能结合在一本书中,以我所知,麦迪森做到了极致。
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很多经济学家。他们获奖的原因要么是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要么是解释了某个人类经济发展史中特别重要的问题,但少有经济学家花费巨大的精力去拼接世界经济两千年纵向横向的历史碎片。这个工作量极其浩大,首先你需要跨国对接,比如将日元、美元和人民币调整到同一个叫做“国际元”的量纲上。把数百个国家拼接到一个量纲上,这已经是个巨大的工程,何况还需要处理时间轴上的工作,要把今天的一块钱和一百年前的一块钱做比较。麦迪森完成了这项开创性的巨大工作,后人也在不断地将其修改完善。
我很高兴我的同事伍晓鹰老师参与其中,向伍老师和麦迪森表示我们的感谢和敬意。
从客观观察到逻辑推论
王全宝:市场上经济史门类的书并不少,请问伍晓鹰老师,《世界经济千年史》最显著的特点是什么?是如何观察经济增长的?
伍晓鹰:麦迪森跳出了原来所有的写法,他并不是从某个主题入手,比如写航海、写枪炮、写细菌、写瘟疫、写国家,以及写各种各样的断代史。这样的主题数量太多,麦迪森没有这样做。麦迪森希望用一个框架将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有机地组织涵盖在一起,同时他希望这个框架本身是有逻辑的,可以通过逻辑推演得到一般化的结论。
严格意义上看,麦迪森终其一生也没能完成这项工作,没能得到一个一般化的概念性的结论。但他提供了相关数据,提供了一个庞大的数据体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人类长期增长的观察。他也做好准备随时接受他人的质疑和挑战,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
接下来就是看能有多少聪明的大脑能把这项工作接续下去。
刘国恩:我补充一点,麦迪森既提供了数据,也给出了他自己基于这套数据得出的对世界经济史发展的看法。这就像我们写一篇学术论文,做实证经济学研究的时候都想尽可能全面、客观地呈现模型分析的结果,而麦迪森则是先开宗明义地给出结果,接下来是讨论,以及基于这样的讨论可能得到哪些结论。
为什么要把结果和讨论两部分开?因为基于讨论部分的内容,不同的学者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conclusion),但结果(result)则相对客观, 它建立在假设和数据的基础上,只有改变数据和基础模型才能改变结果。
伍教授提到麦迪森把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在库兹涅茨的基础上又推后了50多年。库兹涅茨的增长理论认为人类经济在1760年发生大转折,但麦迪森基于相关数据,客观地提出现代经济增长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820年。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并不是因为1820年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而是完全根据客观事实数据得出,这就是麦迪森的风格。
如何理解市场、政府与创新之间的关系?
王全宝:《世界经济千年史》的导言中有这么一句话“一个国家不能在原创性基础上胜出,往往是以国家利益至上扼杀了创新,市场可由政府创造的观点不过是理论上的谴责和历史上的无知,这样的无知就是致命的自负。”请问伍教授,该如何理解这句话?
伍晓鹰:应该把这句话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理解,不必投射到非常具体的事件上去。无论是“举国体制”还是“国家利益”,在历史上美国也有很多类似的行为。当初美国一心想要超过英国,它肯定想了很多办法,也创造了很多类似的词汇。但是口号是一回事,市场是另一回事。市场力量的核心问题是追求效率,大家都知道什么是效率,只要简单对比一下投入和产出就一目了然。如果投入增长5%,产出才增长3%,那肯定亏了。哪怕你资金雄厚,可以吃几年的“老本”,但如果一直无法提升效率,到时候还是得关门大吉。口号不能解决效率问题。
创新源自对效率的追求。大家都去追求效率就会强化竞争,在竞争中暂时落后的一方会想方设法地提高自己的效率,这就会逼出创新。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科学思想,最后能够把科学转化为技术,进而能够让技术商业化才是最重要的。
综合来看,这些环节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中间是市场规律在发挥根本作用。这一过程无法被设计,只有不断创新才是致胜法宝。美国人搞了很多创新,即便是卓别林电影中的拧螺丝的桥段,也是一种生产线和管理方面的创新。只要有一家企业进行了这样的创新,那它就可能给整个行业中的其他企业带来成本下降、产品标准化和生产速度方面的挑战,最终整个行业都从中受益,那些无法跟上潮流的企业就会被淘汰,这就是市场的力量。
在我看来,国家着急,民众热血沸腾,这些都比不上市场的力量作用大。
王全宝:创新还是要让市场发挥力量,刘教授在以往的采访中也特别强调市场的作用。在《世界经济千年史》导言有这么一句话:“国家主义者们并不明白主导全球化的根本因素不是技术而是市场,更不明白决定市场成长的不是国家的力量,而是自然演化的力量。”请问刘教授,我们该怎么理解这句话?
刘国恩:关于经济增长理论,目前大家已经形成高度共识,无论是哪个学派都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两大类条件:一是直接能投入的生产要素,包括资本、人力等,这些生产要素在市场上可以直接购买或者是直接投入;二是靠转化这些生产要素为最终产品的生产率。生产率主要由技术创新决定,技术创新源于新的想法和知识,其源泉取决于技术研发本身所处的制度环境。
伍晓鹰教授曾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反事实思想实验”。从清朝最鼎盛的时候到清朝末年,我们的经济增长为何会大幅下滑,直到最近几十年才打了翻身仗?在我看来,清朝与其他朝代最大的不同就是“文字狱”,“文字狱”最大的打击对象就是思想。思想不进步,知识不更新,技术就难以实现创新,没有技术的创新,生产率就会受到影响。这一逻辑链条直观简单地说明了问题。
沿着这个链条来看伍晓鹰教授提到的“反事实思考”,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国的经济增长从那时开始下滑。那时候的思想受到了约束,想法和知识没办法释放出来,经济增长下滑的结局基本成为必然。
所以今天我们说要坚持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只有这样,我们的思想和知识才能尽情地释放和分享,中国才可能有技术增长源泉,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才能得到保障。
伍晓鹰:我再补充一个例子,在这本书中麦迪森对中国古代的经济问题做过特别精彩的分析。我们都知道郑和的成就,以及那时候中国位居世界前列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那时候我们对海洋各方面的理解也不差,然而最后的结果却是与整个地理大发现失之交臂。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制度,制度不让人出海,最后甚至毁掉造船的图纸,这也值得我们深思。
刘国恩:我曾经读过一位德国经济学家写的关于经济增长的书,他在研究中国的历史时发现,中国的郑和船队比哥伦布早八十多年,郑和船队当时掌握的航海技术也比哥伦布先进不少。比如郑和船队的船在当时已达到长110米,宽50米,每次航行带着成千上万的人员,航行几十个月,多次下西洋,最远的一次到达南非好望角。但很有意思的是,郑和船队到了好望角之后就不再远行。
这位德国学者认为,如果郑和在七次下西洋的过程中,但凡“任性”过一次,比如跨过好望角继续北上,那他可能就会抵达欧洲,中国和世界的版图或将由此改变。然而郑和没有这样做,他死在了第七次下西洋回程的路上。此后大明皇帝就禁止出海,出海甚至成了犯罪,中国与世界可谓失之交臂。
王全宝:创新分为市场创新以及举国体制创新,在两位教授看来,这两者间的关系如何?
伍晓鹰:我并不觉得这两者间该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在我看来,经济学家干经济学家的事,政治家干政治家的事。经济学家通过自己的研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决策参考。当然政策制定者在决策时,也需要平衡各方面情况,找到一种均衡。尽管如此,我认为前面我们提到的“市场的力量”是决策者应当予以尊重的,因为效率才能带来经济增长,倘若不追求效率,任何投入都不会有创新的压力,也无法带来经济增长。
刘国恩:说到大学和创新之间的关系,我想先讲一个创新的概念,再说一组数据。
上世纪3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创新的本质,这是迄今为止关于创新最清楚的概念。熊彼得认为,创新就是创造性地破坏,把现有市场上的东西通过竞争“逐出”市场。这种“驱逐”不是负面的,而是给消费者带来好处的一种机制。这种创造性的破坏,除了借助市场的力量来实现,别无他法。可以说唯有市场竞争,能做到既把市场上现有的东西驱逐出去,还为消费者带来创造性价值。市场的力量才是创新的本质。
北大研究教育经济学的顶级专家闵维方教授,曾在一次讲座里分享过一组实证统计。这项统计的横坐标是欧美大学从其所在国获取政府投入的比重,纵坐标是这些最后形成的专利数,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两者间呈负向关系,即大学从政府拿到的研究基金占比越高,其产出的专利数反而越低。相对应的,当横坐标变为欧美大学从非政府市场、社会竞争性研究获得研究基金的占比,纵坐标依然是所获专利数,二者则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这一组实证统计再次诠释了熊彼得的理论,即创新的本质是市场公平竞争,而非行政部门干预下的竞争。
如何理解科技创新与制度之间的关系?
王全宝:刚才伍教授在演讲当中提到了科技和制度,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生产因素是由技术决定的,比如在农业社会中,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封建社会也是如此。在现在的大数据时代,知识和人力成本也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包括人工智能。那么通过阅读《世界经济千年史》,我们该如何把握科技和制度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伍晓鹰:我们经常把“科学”和“技术”这两个词合并为“科技”来使用,其实科学和技术不是一回事。
科学需要从想法开始,基于创意和想法,提出对自然界的观察;科学也可以从假说开始,某人提出一个假说,看能否证明这一假说,当然其他人也可以否定这一假说。通过对自然界的观察和科学实验,我们可以证实也可以证伪很多假说。一旦认识了自然界的规律,我们就可以对其加以利用。比如我们基于对半导体的认识,制造出了芯片,进而发展出ICT电子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引领未来科技的发展。
从科学创意到技术的出现,这中间必然会经历一个复杂过程,而技术能否走出实验室,能否成功实现商业化,还需要再经历一个重要的过程。技术能否实现商业化,这一点非常关键。
科学无国界,科学思想的传播最终可以刺激技术的产生。一旦技术产生,就可能实现商业化,但是,回到我们的根本问题,要实现商业化就需要市场。虽然中国有巨大的消费市场优势,但如果不完善相关制度,就无法建立真正的市场制度,无法最大程度地激发科学和技术上的创新。
刘国恩:科学是对自然客观规律的认知,我们现在认识得还很少。科学发现本身无法申请专利。
技术是符合科学规律去改造自然的手段,那些能帮助我们提高生产率的技能,我们称其为技术。比如我知道这门技术而你不知道,我就可以利用这门技术,依照客观规律形成更有效的生产方式,这可以申请专利。专利是一种旨在为更多人提供强大激励的措施,它鼓励人们基于科学规律,发现能够提高生产率的手段,并鼓励人们应用技术投资于生产和分享由此产生的收益。
现在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已经与1500年前的技术创新大不相同。中外古代的技术创造、创新,速度都非常慢,包括中国的四大发明。这主要是因为在当时的生产实践中,人们缺乏科学思想的指引,对于现象背后的科学原理知之甚少,只能靠长时间的生产实践去悟出相关道理。现在的技术创新则是更多基于对科学规律的系统认识,通过科学实验获得更快更好的结论。
创新需要投资,有投资就需要有回报,从这个角度来看,针对技术创新的保护非常重要。
伍晓鹰:如果回到王先生主持的这个互动的主题,我觉得当前经济和政策的难题是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把问题的解决交给市场。我觉得麦迪森所勾勒的历史已经给了我们很好的启发。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由政府来解决经济波动,特别是经济衰退问题。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短期问题,而是长期问题,是结构问题。希望由政府投资化解这些问题其实是饮鸩止渴,只能使问题更加严重。更糟的是,政府的出面遏制了市场的功能,阻碍了市场对要素真实成本的评价——要素重新定价,也压抑了政府根本无法替代的市场所具有的学习功能——投资者必须为自己的错误负责,并付出代价。这是个痛苦的过程,政府需要改善旨在保护一个公平和自由竞争的市场所需要的制度建设。除此之外,交给市场,交给企业家,相信他们有足够的智慧重振中国经济。
整理:文展春 | 编辑:王贤青、 白尧